不是前任老婆,我的媳妇儿是初恋。
今天给我的PLR前任发信息,发现该用户不存在,才突然想起两三天前谁跟我说过他要退休了。
真是好快。
起得早,带了一本书到公司看,一般2个小时候后办公室会开始陆续来人,正好有独处时间。翻了两页翻不下去,还是晚上回家看吧
不是前任老婆,我的媳妇儿是初恋。
今天给我的PLR前任发信息,发现该用户不存在,才突然想起两三天前谁跟我说过他要退休了。
真是好快。
起得早,带了一本书到公司看,一般2个小时候后办公室会开始陆续来人,正好有独处时间。翻了两页翻不下去,还是晚上回家看吧
延续2025年的风格,记录一下一年读的各种书
1月27日,《邓小平时代》,去年买的,花了好长时间才看完,我觉得我看得慢了。
趁着这次长假,把很早就想做的一个实验室重新捡起了做了一遍,不过还没做完。
明天要上班了,天也黑了,准备去吃点东西回家。
这几天感谢deepseek和豆包一直帮我一起学习,看着满屏幕的pde*, pte*, pgdir, va, pa, PTE_P, KADDR,,,,, 很难相信这是我写的代码。
本来想着最后一天去滑雪的,想想算了,今天还是把连着的几个实验做完的好,这样比较系统和完整。
祝大家开工大吉!
当你写完一圈代码,下楼去买咖啡的时候,发现,哈,才十点半。
另外,我的实验室1终于做完了,撒花:)
今天国内上班了,也摸到公司来继续做我的实验。不太想处理welink的信息,也幸而没什么人找我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有点饿了,决定去国泰吃个中餐,想想这几天好像没正经吃饭,越想越饿哈哈。
走到大街上有点吃惊,原以为过节的街道会冷冷清清,特别是“过年”(俄罗斯的圣诞节是1月)这种大节,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七八点钟吧,基本一个人没有,这一下子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。
去国泰的路上要路过阿尔巴特大街,吃完回来决定沿着我和大力同学经常吃完早饭遛弯的那一条路走走,下雪了,灯光也布置得很好看,熙熙攘攘的人群,有点像一些电影里的冬日大街桥段,还挺美。电影果然源自生活。
路上收到几个小花花的信息,这姑娘一天天长大咯,愿大家快乐、健康。
这本书好厚,700多页,看了一段时间了。今天翻到一个特别的书签,应该是小花同学捡回来的叶子,所以先拍照记录一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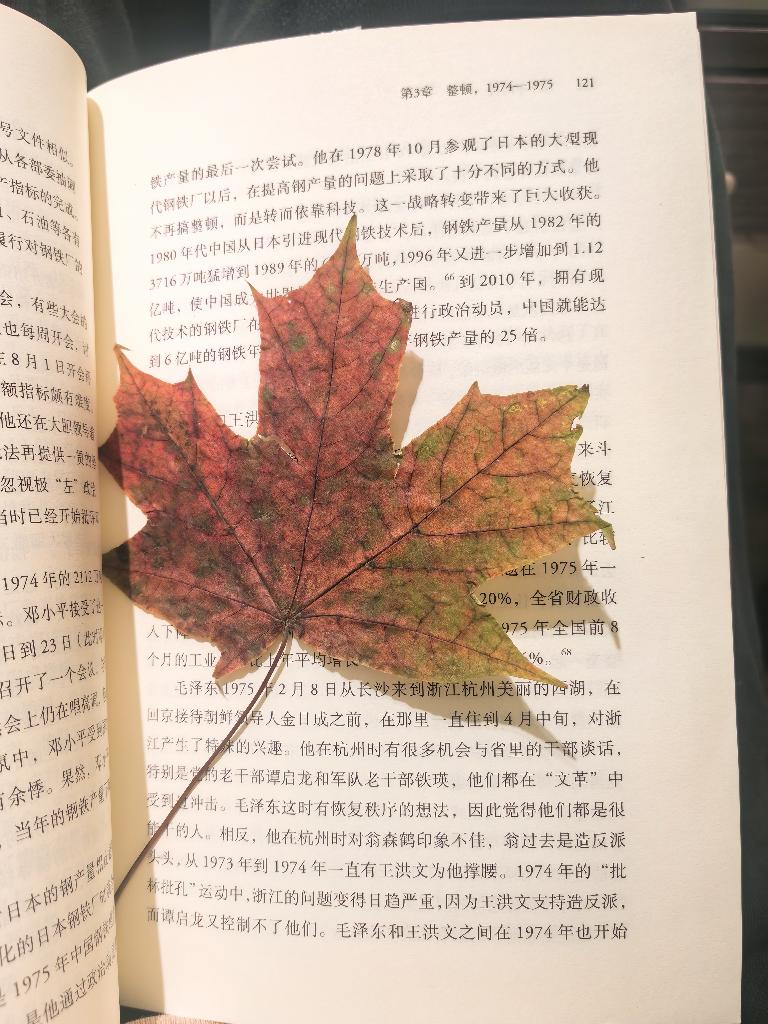
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热爱出差,但我依然热烈的喜欢晚上独处小酌和看书的时间,甚至有些傲娇。我猜用不了十年,两三年后如果读到现在的文字,都会觉得可笑,不过当下确实欢喜—娃娃们和妈妈去埃及度假了,自己找了个小酒吧,一张小桌子,两杯酒,一个焦糖布丁,外加打发时间利器—一本书。我在这儿待了快两小时了好像,并不会有只喝酒带来的无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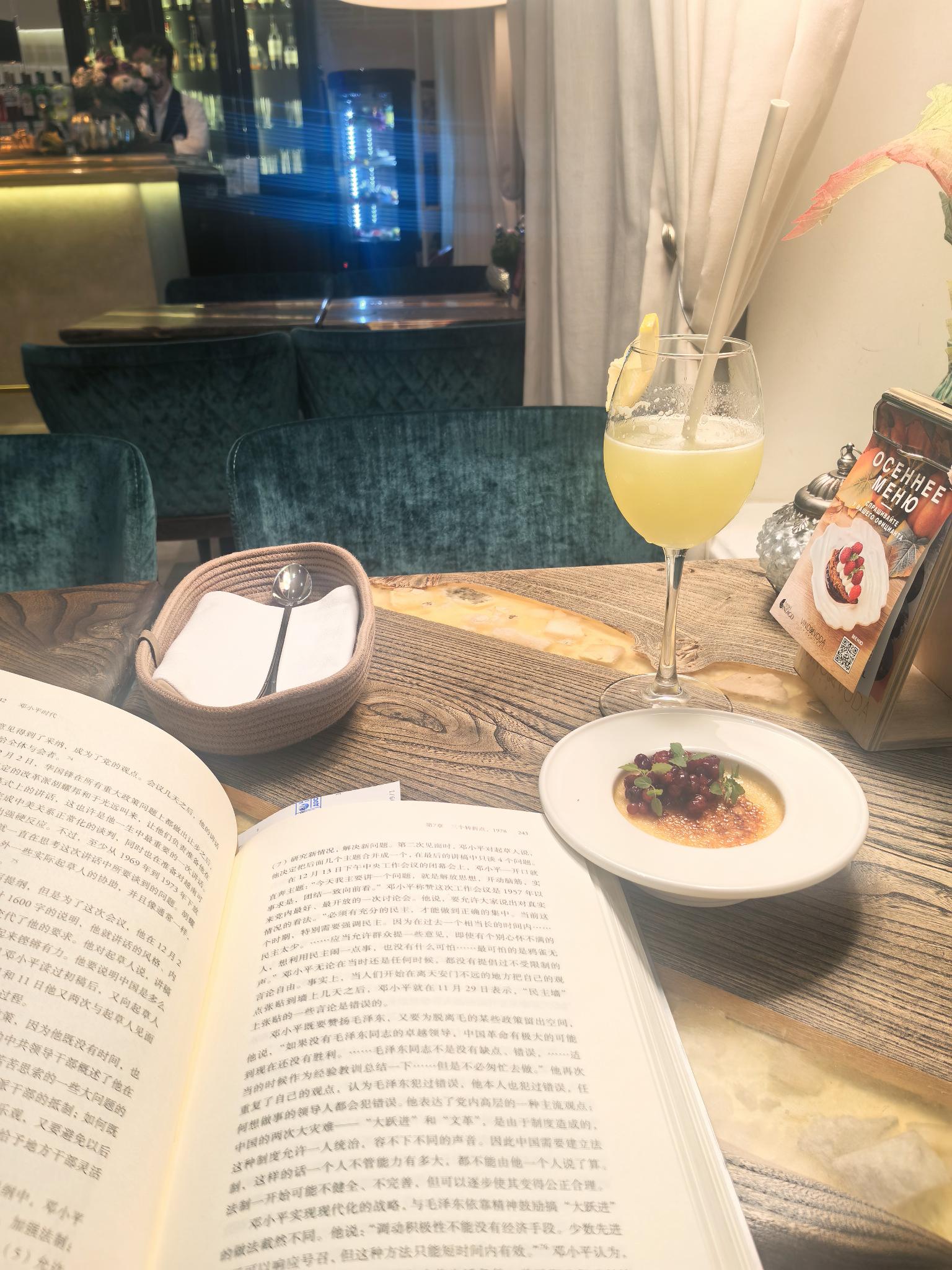
在这里我看完了书的第七章—三个转折点。
11月四号,周二,今天是莫斯科放假的日子,国内没放假,有个会需要到公司开,就带着书过来了。看完了中美建交的这一部分,感叹时隔30年,在多方努力下重新关系正常化所经历的坎坷和深远的影响,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1979年的这一次不算革命的革命,把中国的发展推向了快车道。幸亏我们有英明的领导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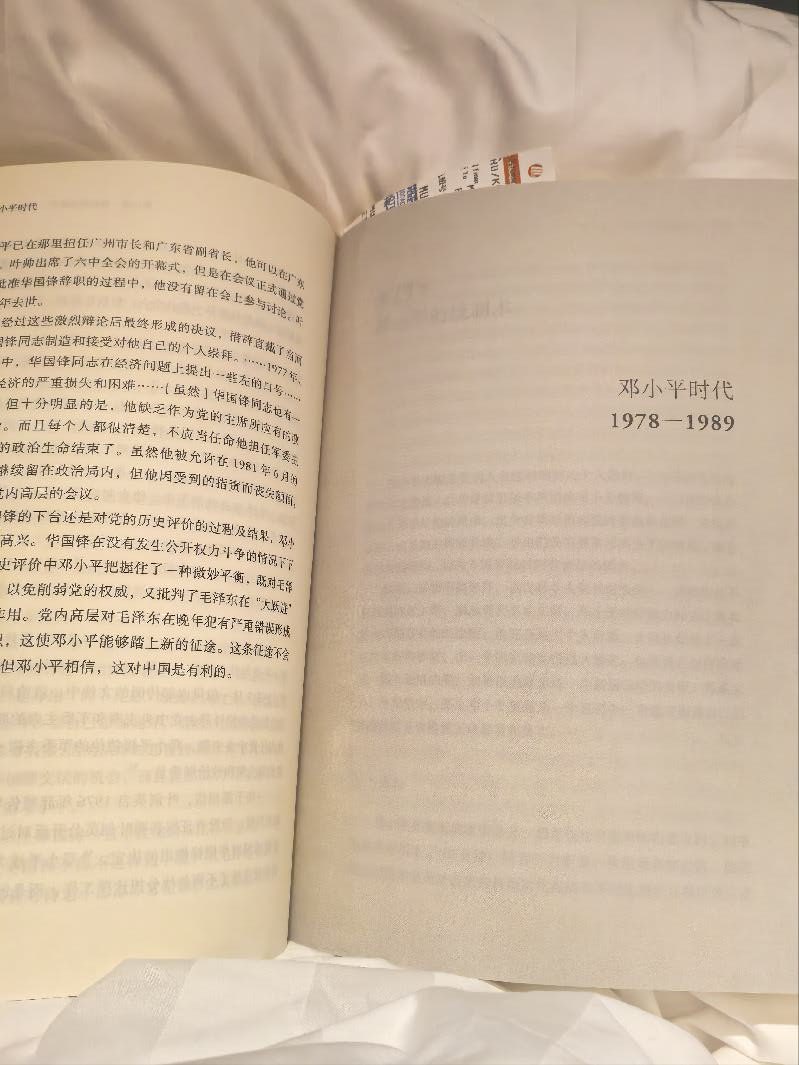
在2025.11.12 凌晨两点醒了摸起来,到现在凌晨4点整,在看到368页以后,看完对华国锋的下台和对党的历史评价的过程和结果后,终于来到了与书名同名的大章节《邓小平时代》。
12月30号,看完了这一同名章节《邓小平时代》,章节最后已胡耀邦的下台和赵紫阳的十三大亮相结尾,这大概也是邓小平和陈云等老同志完成接班人培养的一个标志。现在是凌晨06:49:38,好像是4点就醒了,折腾了一会儿决定起来看看书。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机会把整本书看完,除开注释大概还有100页,三个章节,希望能看完吧。
2026年1月27号,睡觉前把最后剩的几页看完了,记得是661页一共,再往后就是注释了。看完顺手放在《兄弟》上面比了一比,大概宽1/4,厚1/4到1/5的样子,印象中再读过这么厚的好像就是《叶卡捷琳娜》那本了。下一本是啥呢,今天想想。
完结,撒花。
这本书看得我云里雾里,特别是前面几章节,突然醒悟原来他们说的多种叙事手法指的就是——叙述的时候时空跳来跳去。绕得我是一头雾水,搞不清楚当前写的“我”是死的还是活的,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已经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/她,然后就觉得,是自己的水平还达不到看这本书的要求。当然,我也挣扎了一下,觉得是这些文学奖作品都是学院派的那种故作高深。
要我推荐的话,我是不推荐的。